 哲学逻辑
哲学逻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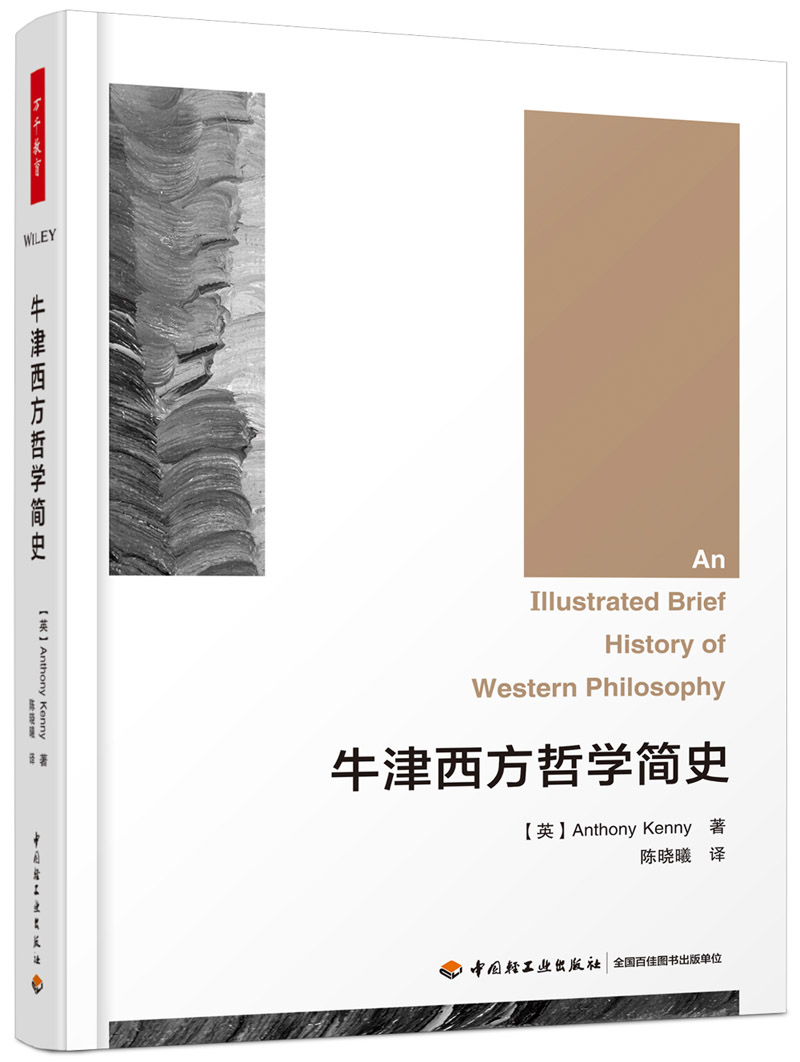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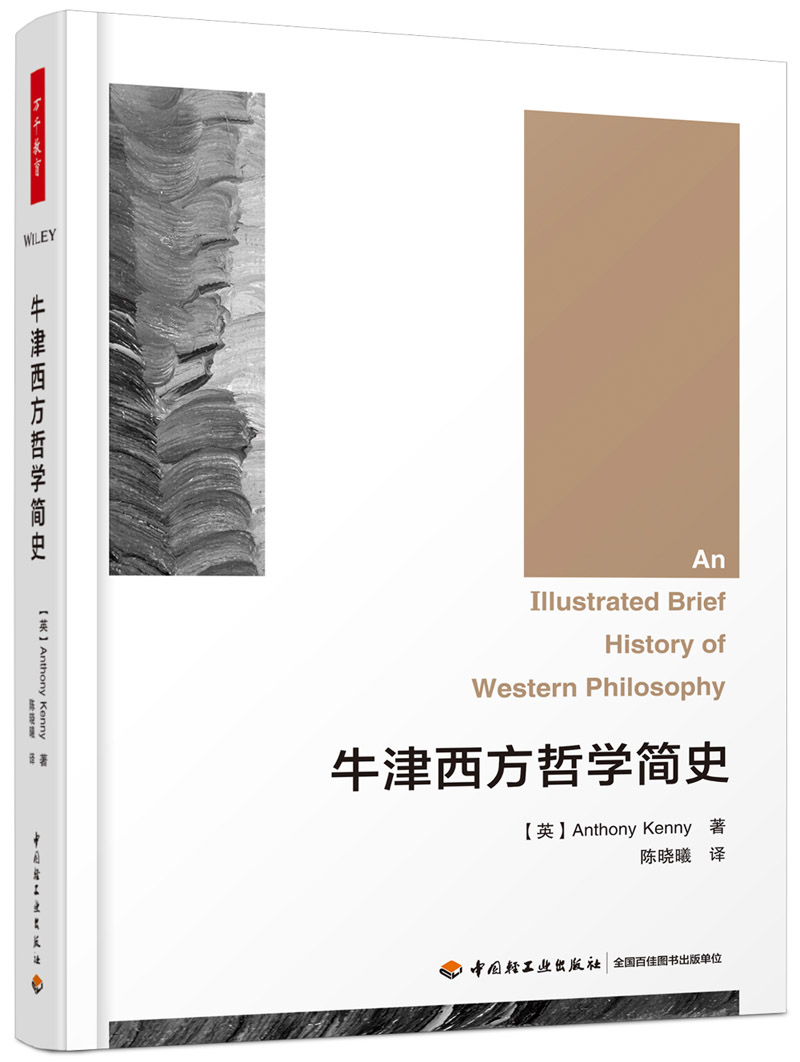

这是一部在行文风格上可与罗素《西方哲学史》媲美之作。面向未经专业哲学训练的读者,作者在本书中极力避免未加解释地使用任何哲学术语或只给出哲学学说概要,代之以详细铺陈哲学家出场的时代背景,对晦涩的哲学观点给予生动的解释,对个别哲学家的逸事进行饶有趣味的讲述,并对主要哲学论题,说明不同哲学家采取的论证方法,给出作者自身有针对性的评注。
这也是一部严谨的哲学史著作。为弥补罗素哲学史一书欠精确之处,作者对在西方哲学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流哲学家的思想给予了全面阐释,展示不同哲学家就同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并详述中国读者缺乏了解的中世纪哲学、宗教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等,使得本书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之作。
这种严谨又不失生动的写作方式必能帮助普通读者走近那些伟大的心灵,掌握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尝到阅读哲学书的兴奋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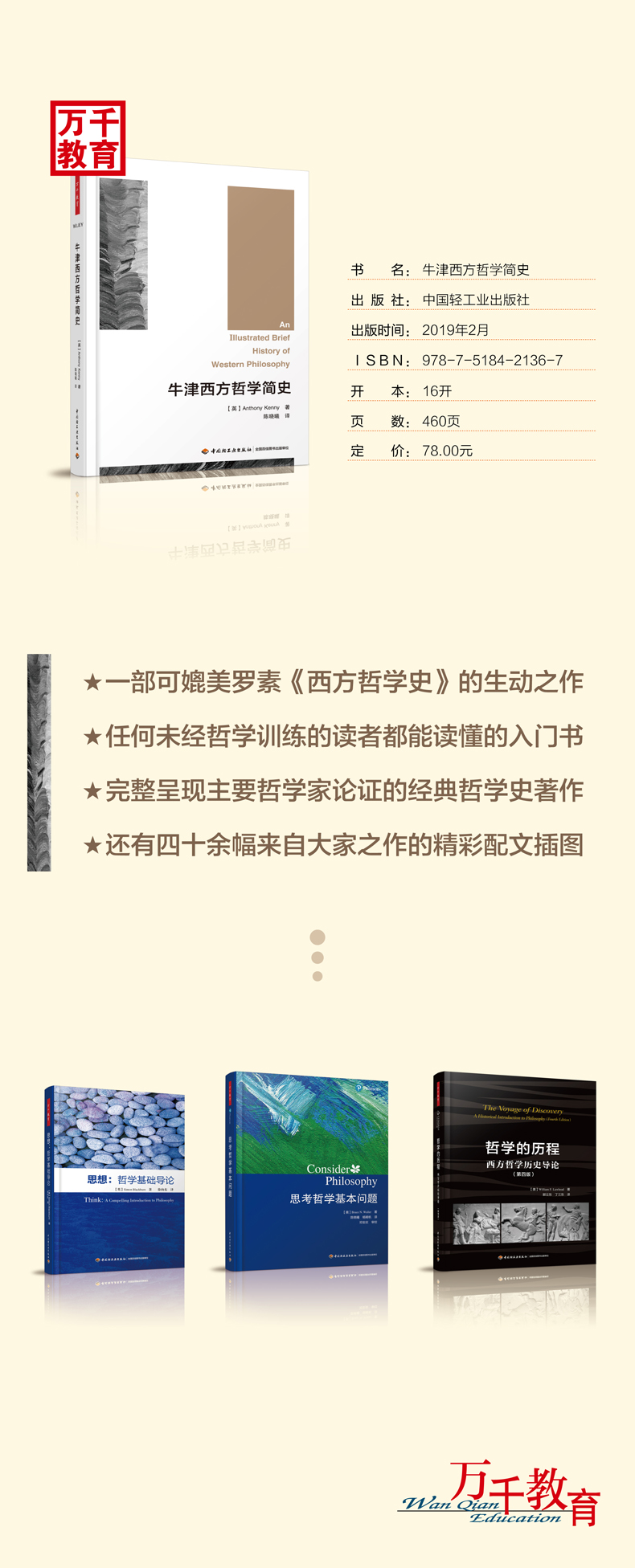
一部风格之作:引人入胜的写作方式让人初尝阅读哲学的兴奋滋味
简明入门之选:避免未加解释地使用任何专业术语来介绍哲学观点
严谨的哲学史:完整呈现主要哲学家的论证并给出有针对性的评注
精选配文插图:来自大家之作的四十余幅插图让内容更加通俗易懂
作者简介
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 1961年于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讲师(1963—1964)、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研究员(1964—1978)、贝利奥尔学院院长(1978—1989)、牛津大学副校长(1984—2001)、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1985—1988)、大英图书馆委员会主席(1993— 1996)、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1989—1993)等,也是英国与美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史、维特根斯坦哲学、心灵哲学及宗教哲学等。著有40余部著作,包括《行动、情感与意志》(Action,Emotion and Will,1963)、《笛卡尔》(Descartes,1968)、《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7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The Aristotelian Ethics,1978)、《阿奎那》(Aquinas,1980)、《弗雷格》(Frege,1995)、《牛津西方哲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2000)、《维特根斯坦读本》(The Wittgenstein Reader,2005)、《牛津西方哲学史》(四卷本)(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2012)等。
译者简介
陈晓曦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滁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学思想史等,译有《思考哲学基本问题》,发表有20余篇文章。
1945年,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了单卷本《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该书至今仍在被人们阅读。有人建议我来写一部当代风格之作,与之颉颃。起初我几乎被此挑战吓倒。罗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有谁胆敢冒险与他媲美?但是,他的哲学史著作并未被普遍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因不公正地对待以往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饱受诟病,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康德(Kant)等。而且,他关于哲学的本质和哲学方法所采用的假定,也受到当下大多数哲学家的质疑。看起来确实需要一本书,从当代哲学视野出发全面概述这一主题的历史。
尽管罗素的著作在细节上有欠精确,但依然不失趣味并引人入胜。该书让许多人初尝阅读哲学的兴奋滋味。在这本书里,我的目的是产生与罗素的著作同样多的受众:我为受过普通教育的读者而写,他们没有受过特殊的哲学训练,但希望明白哲学曾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尽力避免不加解释地使用任何首次出现的哲学术语。柏拉图(Plato)的对话集在这里就是一个范例:柏拉图能够不用任何专业词汇就提出哲学论点,因为在他写作之时,尚未有任何哲学概念存在。有鉴于此而非其他的缘故,在本书的第二、三章,我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探讨了他的几篇对话。
我一直竭力想摹仿罗素的行文,主要是出于其明晰与充满活力的风格。他曾写道,作为散文家,其楷模是贝德克尔(Baedek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与哲学素昧平生的读者注定会在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感觉理解有困难。哲学并不存在肤浅的目标,每一位新手哲学学者都必须奋力昂起头,以免溺水。但我已尽最大努力,确保读者在理解上不必面临任何困难,除非那是主题自身本质所内含的。
事先解释清楚哲学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学习哲学最好的方法是阅读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本书打算向读者展示什么话题曾让哲学家感兴趣,以及他们用了什么方式来加以阐明。就其自身来说,哲学学说的概要论述几乎无甚用处:单单是告诉哲学结论而不说明哲学家达到结论的方法,这是欺骗读者。出于这个缘由,我尽力去呈现批评哲学家在论证他们的命题时所采用的推理。我这样与过去的伟人争论,不是出于不尊重。这乃是严肃对待一位哲学家的方式:不当他文本的应声虫,而是应战它,从其力量和不足中汲取教益。
哲学同时也是最令人激动与最令人沮丧的学科。哲学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她是所有学科中最广泛的,探究贯穿于我们就任何话题讨论与思考的基本概念。而且,哲学活动还承诺不需要任何特殊的预备性训练或指导;任何人只要愿意深思并遵循推理的脉络都可以进行哲学活动。不过,哲学也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不像科学或历史等学科,哲学不提供关于自然或社会的新信息。哲学并不旨在提供知识,而是理解;哲学史表明,即使对那些最伟大的心灵而言,发展出一种完整而连贯的洞见是何等的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没有一个人已经成功地,对我们用来思考最简单思想的语言本身,达到一种完整而连贯的理解。因此,被很多人看成是作为自我意识规训的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Socrates),也宣称他所拥有的唯一智慧就是自知自己无知,这也并非偶然了。
哲学既非科学,也非宗教,尽管哲学与这两者在历史上一直纠缠着。我努力呈现诸多领域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从宗教反省中脱胎并演进到经验科学的。被过去伟大哲学家处理的很多论题在今天看来已不能算作哲学问题了。与此相应,我会聚焦他们曾致力思考过并在今天依然被看成属于哲学的领域,诸如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心灵哲学等领域。
像罗素一样,我对历史长河中的哲学家及其历史贡献做了选择。不过,我没有像罗素那样,大幅度偏离哲学标准范围内已普遍接受的内容。如他一样,我也加入了对哲学思考有影响的非哲学家的讨论,这就是为何达尔文(Darwin)、弗洛伊德(Freud)的名字也被列入目录中的原因。我致力于把相当大的篇幅给予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尽管这没有罗素花费的篇幅多,罗素的著作写到中间部分还未到阿尔昆(Alcuin)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且未加深入。我则一路而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未包含20世纪的欧陆哲学。
还是如罗素一样,对哲学家的生活,我也勾画了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背景:年代愈久则篇幅愈大,而逮至当代则随之简略。
此书不是为专业哲学家而写,当然尽管如此,我也希望他们会发现我的作品是准确的,也能将此书作为背景阅读材料推荐给他们的学生。对那些已经熟悉该主题的人而言,我的写作自然打上了我本人哲学训练的烙印。这种训练首先体现在从中世纪汲取灵感的经院哲学,其次体现在语言分析学派中,而语言分析学派在英语世界里主导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我出版这本书的希望是,它可以向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人传达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激动人心之处,并将他们引向过去伟大思想家的实际著作。
我深深感谢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以及为准备此书而给予支持的安东尼·格雷厄姆(Anthony Grahame),还包括三位匿名的审阅人,他们为这本书的完善提出了有益建议。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南希·肯尼(Nancy Kenny),她通读了全书的手稿,删除了许多非哲学专业者难以理解的段落。我相信我的读者也会分享我对她的感激,因为她为读者免去了无益的辛劳。
1998年1月
我感谢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欧文(D. L. Owen)博士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克赖纳(I. J. de Kreiner)博士,两位为本书第一版指出过许多小瑕疵。
2006年1月
尼采
在19世纪,所有克尔凯郭尔的观点都被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hce,1844—1900)夸张地全盘否定了。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感性享受是最低级的个体生存形式,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则是最高级的个体生存形式。但是,尼采却把基督教视为人类理想最低级的贬低,人类理想在纯粹的感性价值中找到其最高表达。
在经历了虔诚的母亲和姑姑们路德式的养育后,当1865年在莱比锡大学偶然接触到叔本华的无神论时,尼采顿有解放之感。此后,他一以贯之地表现为一个基督教气质和耶稣人性的反对者。他有关艺术是人类活动最高形式的信念在他自己的哲学风格中表现出来,这种风格是诗意的、格言的,而非辩论性的或演绎的。当尼采24岁时,他被邀请到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讲授语文学(philology)[“philology”是语文学,又叫传统语言学,其单词外形与“philosophy”(哲学)的单词外形相似,但毕竟不同,不少汉译尼采作品都把“philology”误译成了“哲学”。——译者注]。他把他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献给了理查德·瓦格纳。在该书中,尼采对希腊精神(psyche)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狄俄尼索斯(Dionysus)代表的狂野、非理性的激情,阿波罗代表的规训良好的、和谐的美。希腊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这两者的综合,当然后来被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扰乱。现在的德国人只有向瓦格纳寻求解脱之道,才能从颓废中拯救出来,并超过希腊。
1876年,尼采与瓦格纳决裂并不再赞赏叔本华。在《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all too Human)一书中,他一反常态地同情功利主义的道德,似乎认为科学的价值高于艺术。但是,他将其哲学的这个阶段视为某种像蛇蜕皮一样的东西。1879年,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后,尼采开始写作一系列肯定生命价值的著作,痛斥基督徒的自我否定、利他主义伦理学、民主政治和科学实证主义等,因为它们都敌视生命。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快乐的知识》(Joyful Wisdom,188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1885)、《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1886)、《道德的谱系》(The Genealogy of Morals,1887)。1889年,他开始显出发疯的迹象,遂过着衰老退休的生活,直到1900年去世。
尼采相信,历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道德。贵族们感到他们自己属于比同类更高的层次,使用像“善”这类词语来描述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以及他们的特征:出生高贵、富有、勇敢、诚实、金发碧眼。他们鄙视其他人,认为他们粗俗、下流、懦弱、不忠以及皮肤黑,并把这些特征看成“恶”。这是主人的道德(master-morality)。穷人和弱者,怨恨贵族的权力和财富,建立了对立的价值体系,奴隶的道德(slave-morality)或民众的道德(herd-morality),高度重视诸如谦卑、同情和仁慈等对压迫者有益处的特征。这种新体系的建立,尼采叫作“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并且把它归诸于犹太人。
只有犹太人,处在贵族等式(善=贵族的=美的=幸福的=为诸神所爱的)对立面的犹太人,敢于以其可怕的逻辑提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等式,并且刻骨憎恨(虚弱的憎恨)地坚持着对立等式,即“只有可怜的不幸者、穷人、弱者和地位低下者才是善的;痛苦的人、匮乏的人、生病的人和看起来令人厌恶的人是虔敬的,是唯一被赐福的,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得救赎——但相反,你们这些贵族,这些权贵们,永远都是罪恶的、恐怖的、讨厌的、贪婪的、不信神的,你们将永远不会被赐福,而是被诅咒和谴责!”。
尼采说,奴隶的反抗始于犹太人,现已取得了胜利。仇恨的犹太人在基督爱的福音面具下取得了胜利。在罗马人那曾是贵族美德的典范,人们现在对四个犹太人毕恭毕敬:耶稣、彼得、保罗和玛丽。结果,现代人只是一个侏儒,失去了成为真正的人的意志。粗俗和平庸成为规范:唯有在如拿破仑身上尚闪现着贵族理想。
善与恶对立是奴隶道德的特点,目前还支配着他们。贵族蔑视民众为坏人,但奴隶则怀着更大的敌意,谴责贵族不仅坏而且有罪。我们必须对奴隶道德的统治进行斗争:方法就是超越善与恶的界限,引入价值的第二次重新评估。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作为主奴之正反题的合题,将出现超人(Superman)。
超人将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尼采说,人们开始认识到基督教不值得信仰,以及上帝死了。上帝的概念已经成为人类生命完善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我们的生存意志。但是,我们的生存意志一定不会如叔本华所谓的颂扬弱者,它必须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在尼采汉译作品中有“强力意志”和“权力意志”的不同译法。从本书看,尼采的原意是“走向(获取)权力的意志”,即强者自定义善恶,而不是以弱者、奴隶的标准作为善恶的标准。——译者注]。权力意志是一切生命的秘密,每一生物都寻求释放自己的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知识仅仅是权力的工具,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而只有更好或更糟地强化生命的虚构。快乐不是行动的目的,而只是权力运用的意识。人的权力的最大实现将是创造出超人。
人性(humanity)只是通向超人的一个阶段,后者是大地的意义。但是,超人不是通过进化而达到的,而是通过意志的运用。“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注定是(is to be)大地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你们必定能创造出超人!也许不是你们自己,我的兄弟们!但你们能将自己改造成为超人的先人和远祖:让这成为你们最美好的创造吧!
超人的到来将会是世界的完美之物,但它不会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尼采坚持永恒轮回学说(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历史是循环的,一切发生过的,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都会再次发生。
要冷静地评价尼采是困难的。他对其他人不公平的批判,令读者对他自己的作品产生了相应的急躁情绪。比如,在他的最后著作《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评价他的早期作品说:“写得蹩脚、拙劣、使人难堪。比喻既空洞又混乱。它缺乏逻辑的精确,对自己的主旨如此自信以至什么证明都不要了”。
尼采没有对他所批判的传统道德观给出相当一致的表述。尼采对超人的本性描述得过于粗略,以至无法提出任何标准来对人类的德性和罪恶做出判断。在诸如对残忍之类的评估中,要发现尼采自己的立场是很困难的。当尼采谴责宗教及其在奴隶道德之罪中所起的作用时,他满怀雄辩的义愤,描述那些执拗者和迫害者施加的痛苦遭受和野蛮折磨。但是当他描述他的贵族的“金发碧眼的猛兽”之肆虐时:
他也许历经反复的谋杀、纵火、强奸和酷刑等类似恐怖,虚张声势,又故作道德心安,好像仅是狂野学生的恶作剧在上演,完全相信诗人如今有着歌唱和庆祝的充分主题似的。
他似乎把这视作微不足道的过失,是其热情奔放的高贵精神的必然产物。把尼采最后的精神错乱视为贬损其哲学的理由,这是缺乏哲思的。但另一方面,要同情一个把同情(pity)视为一切情感中最可鄙的情感的人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