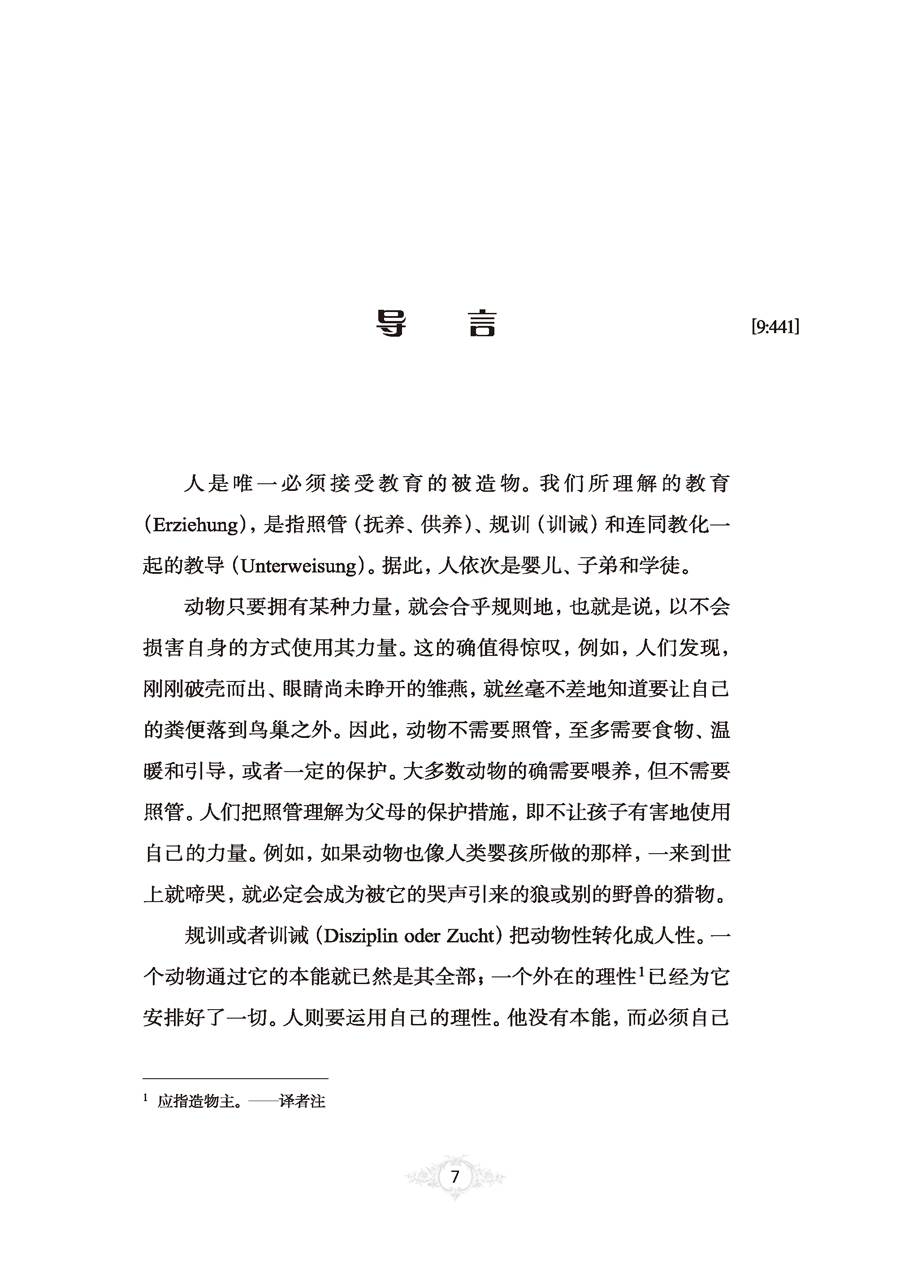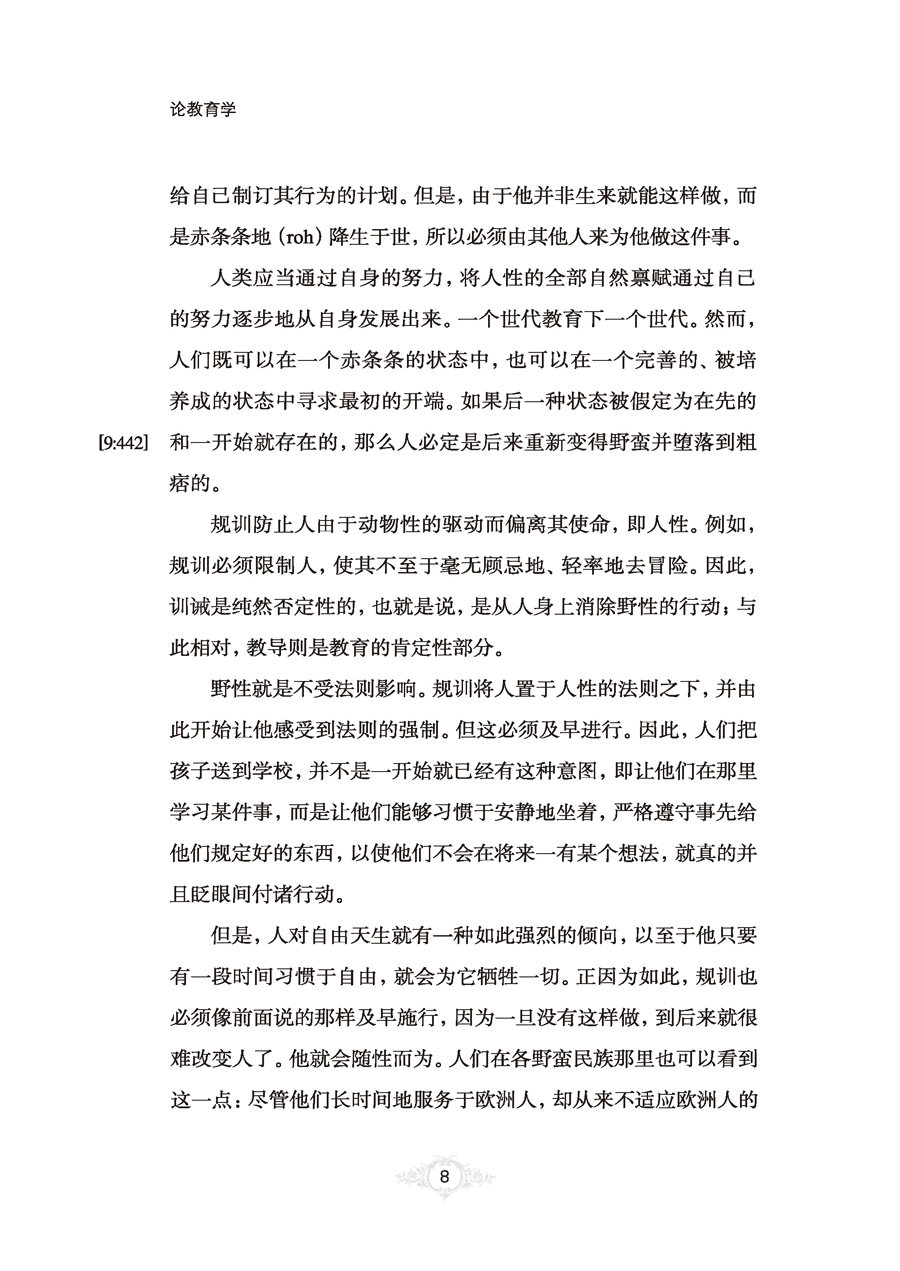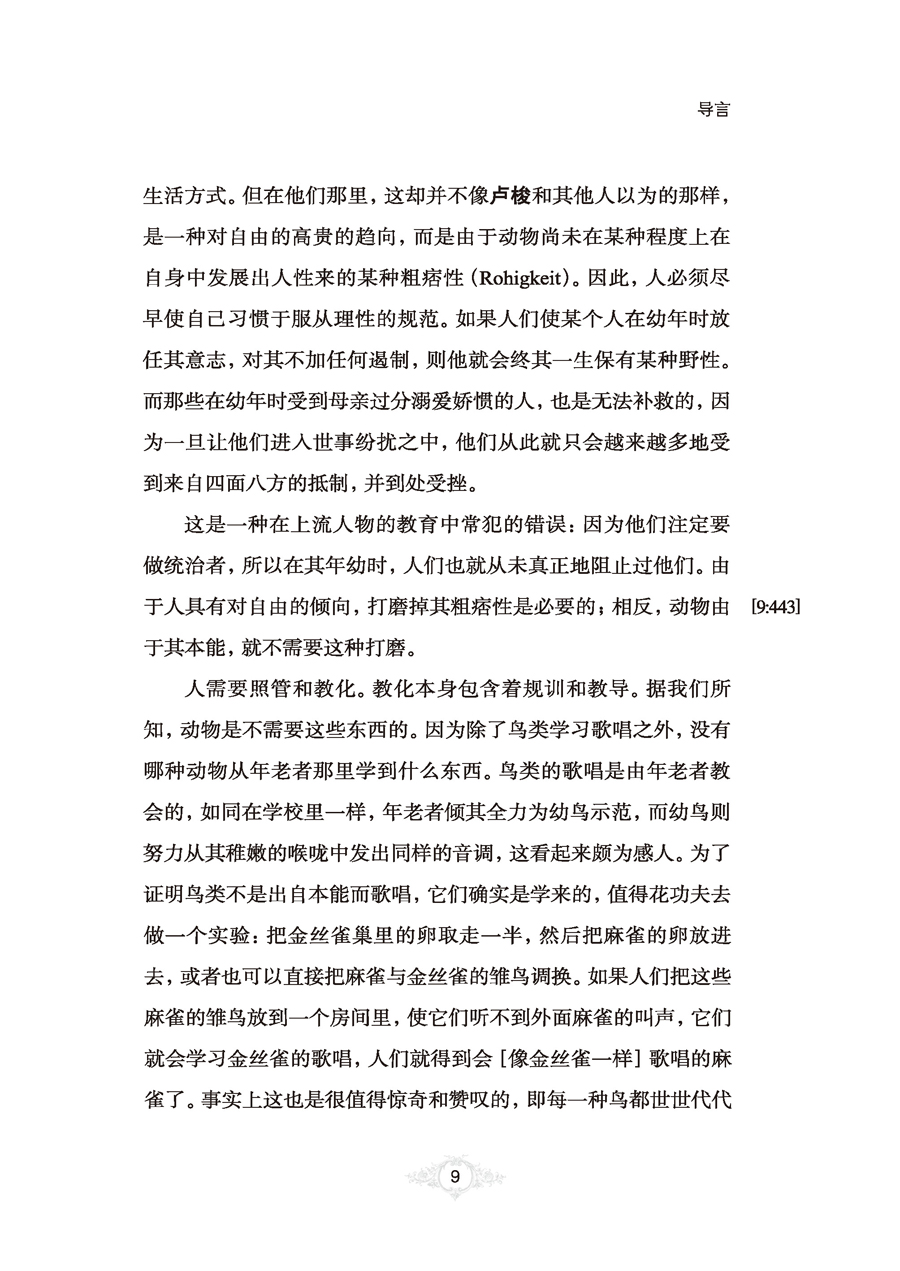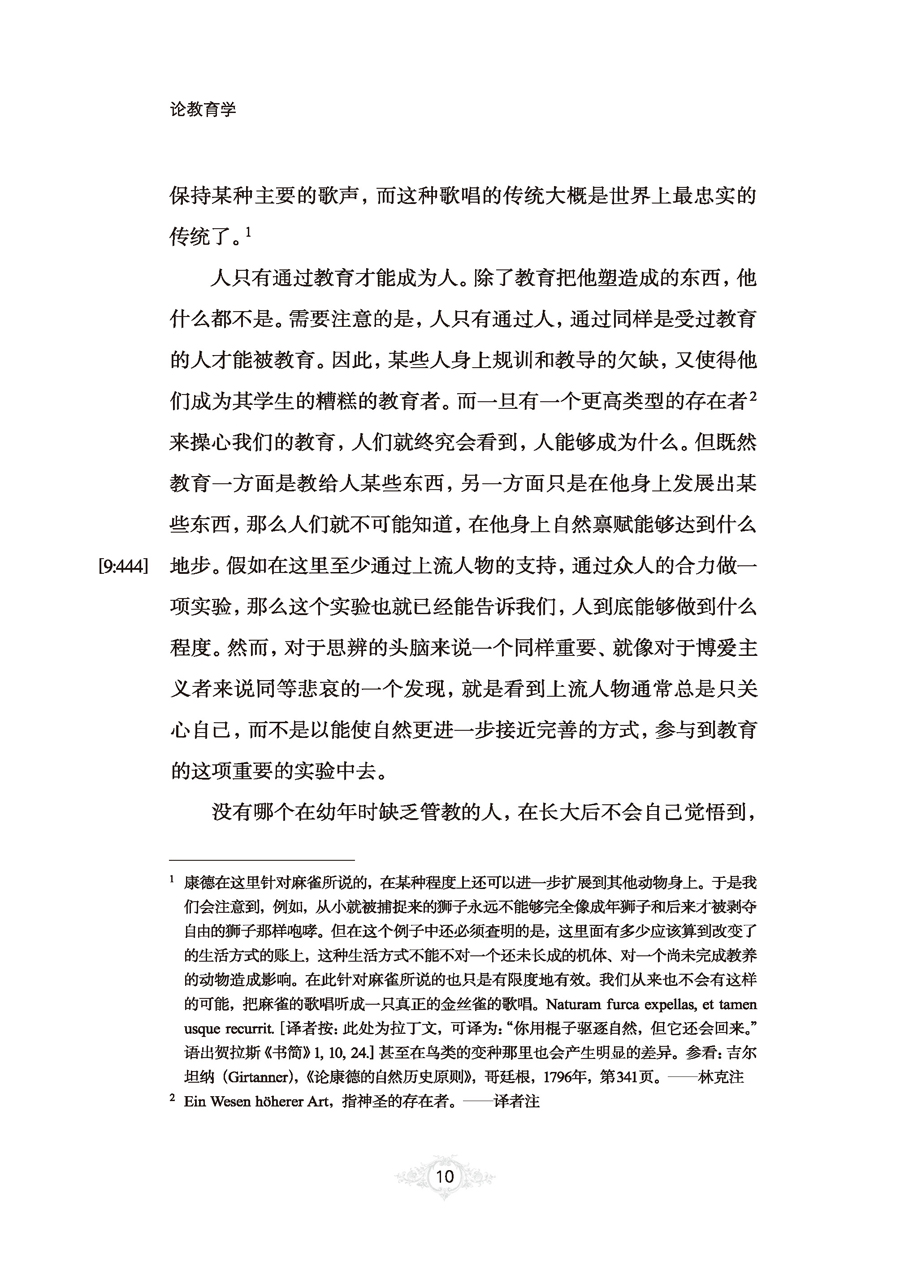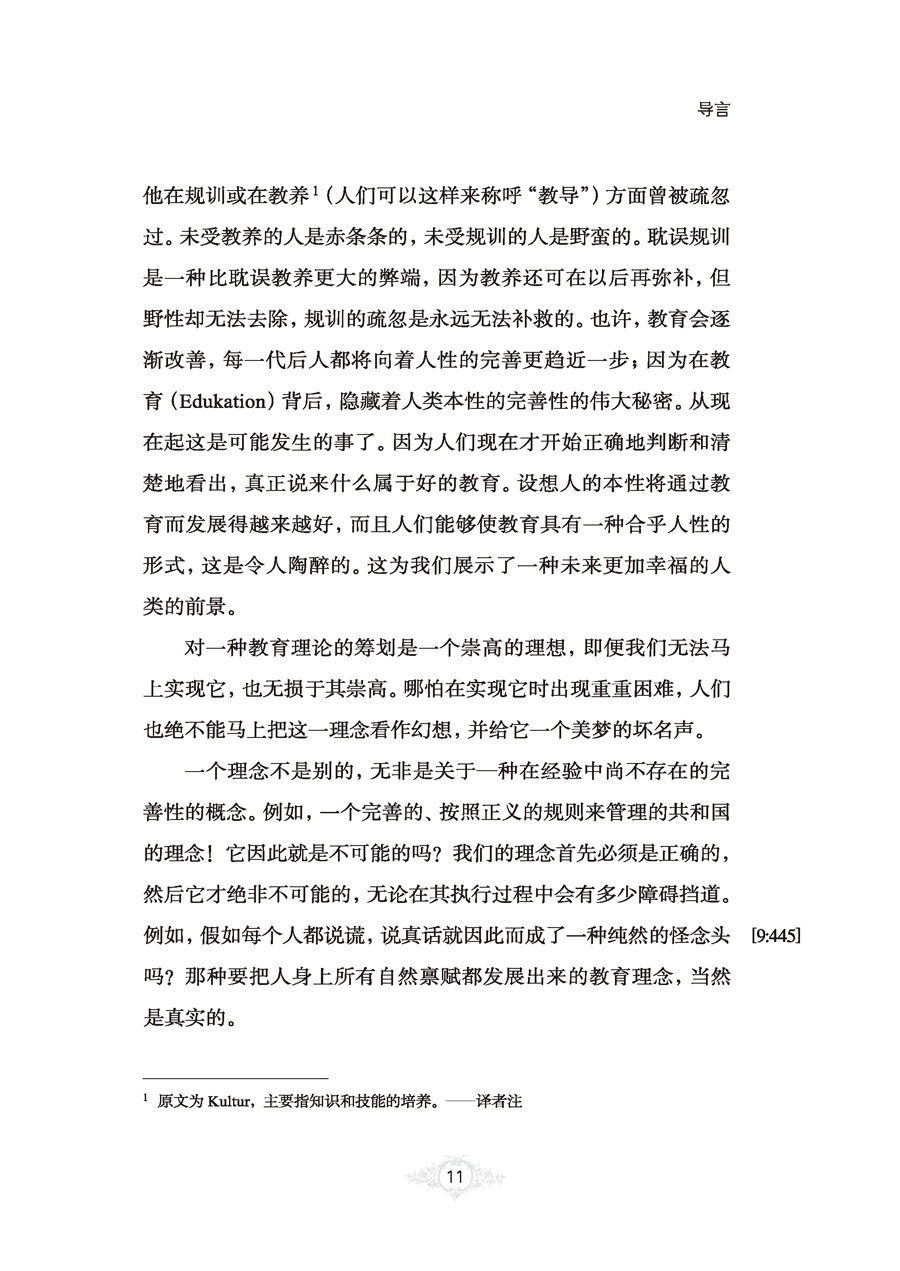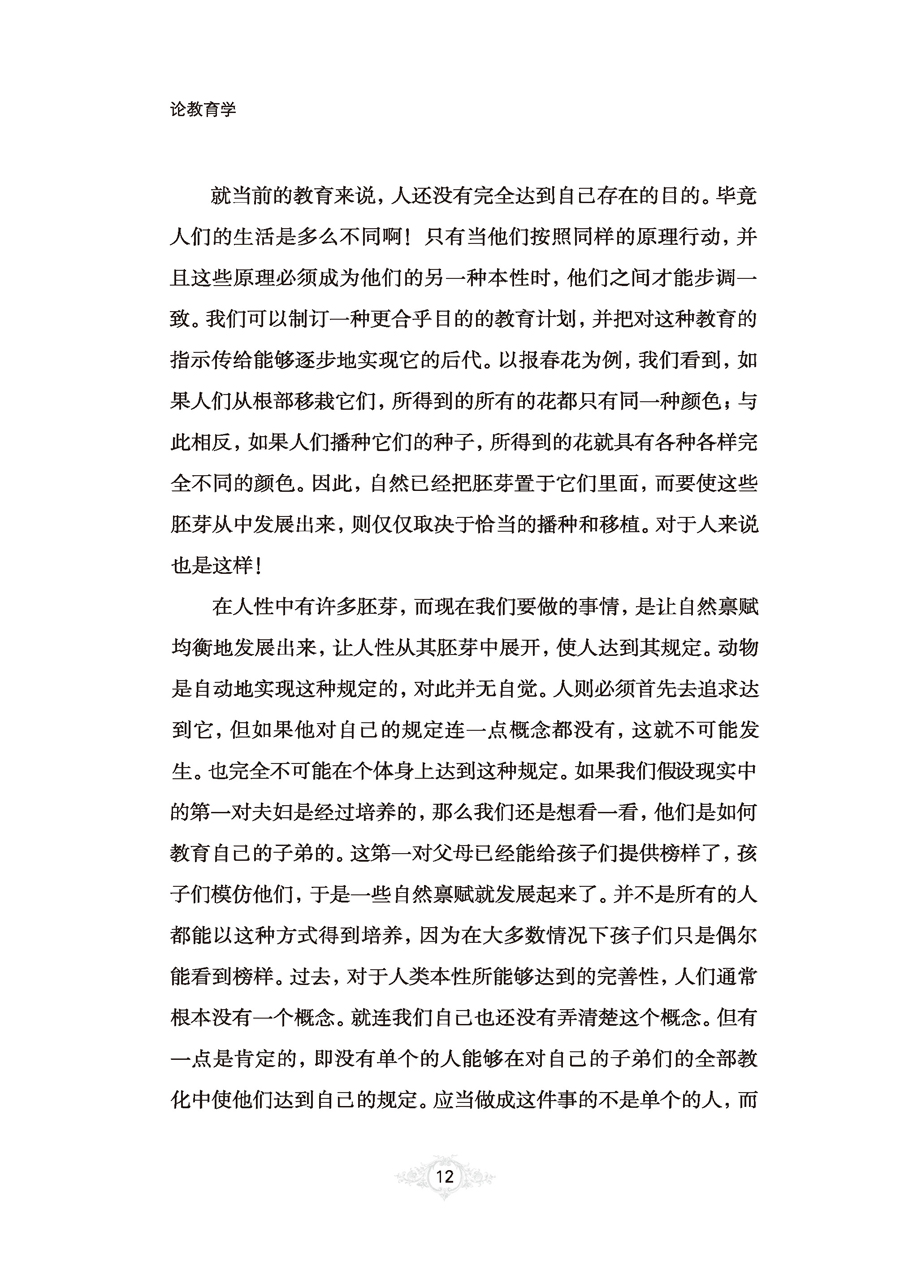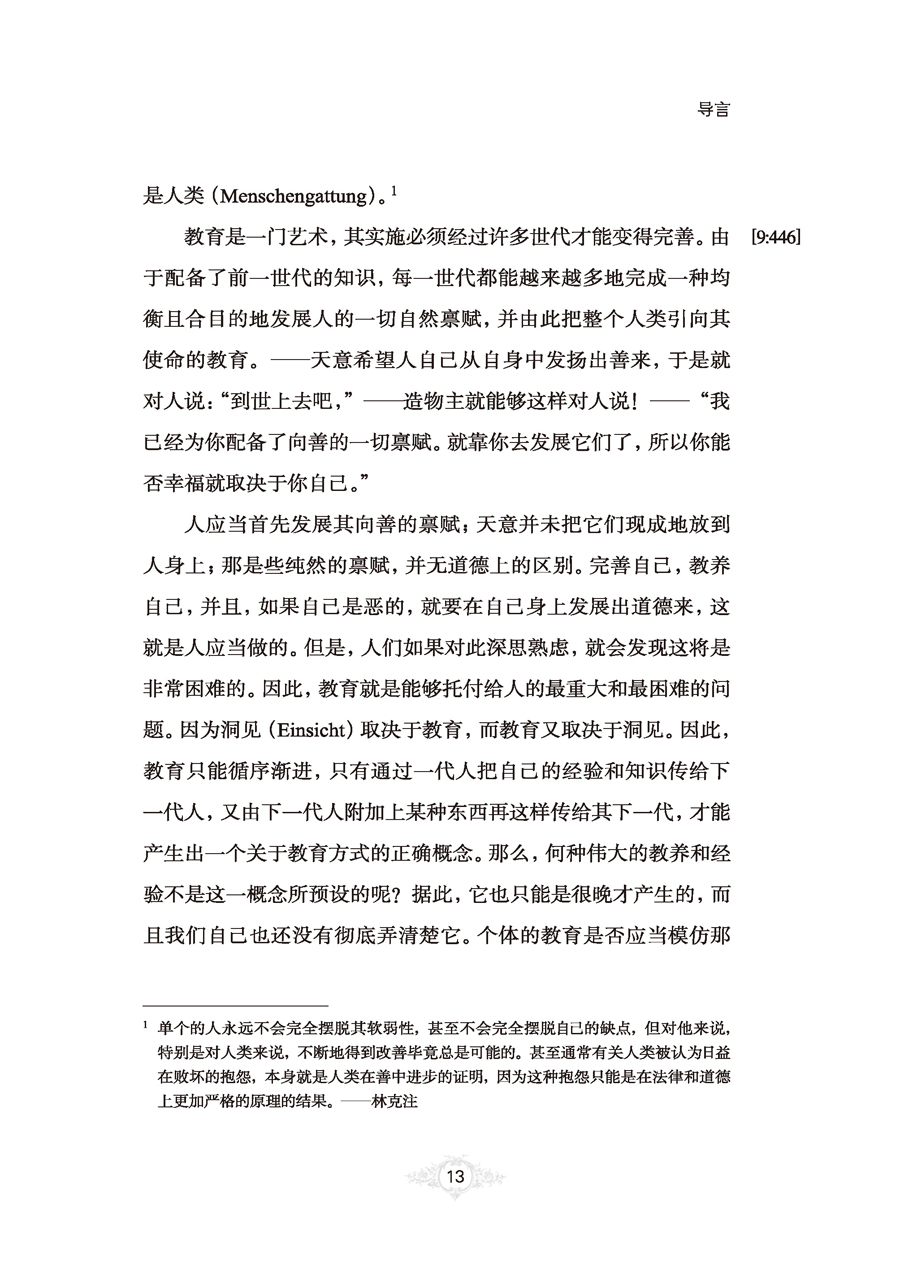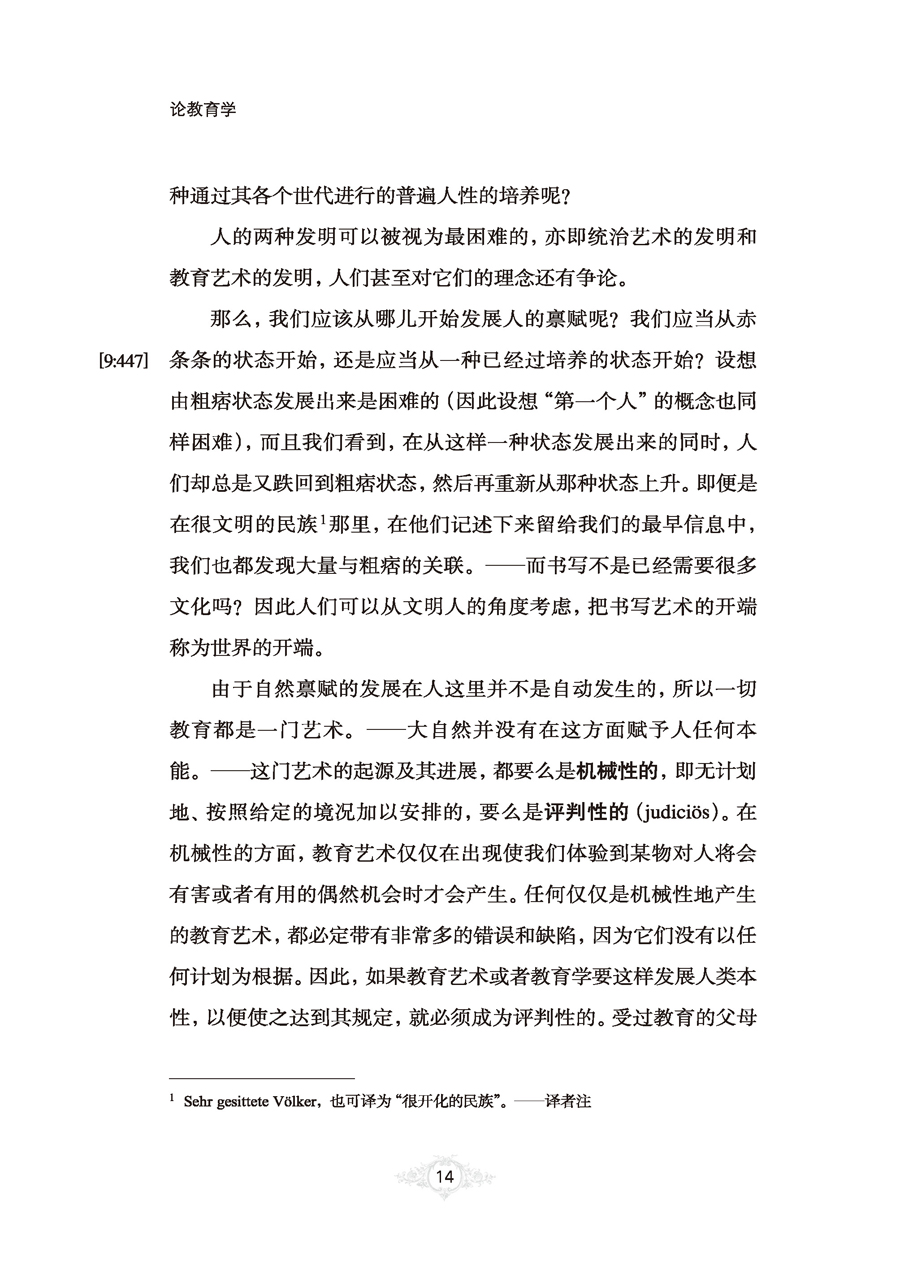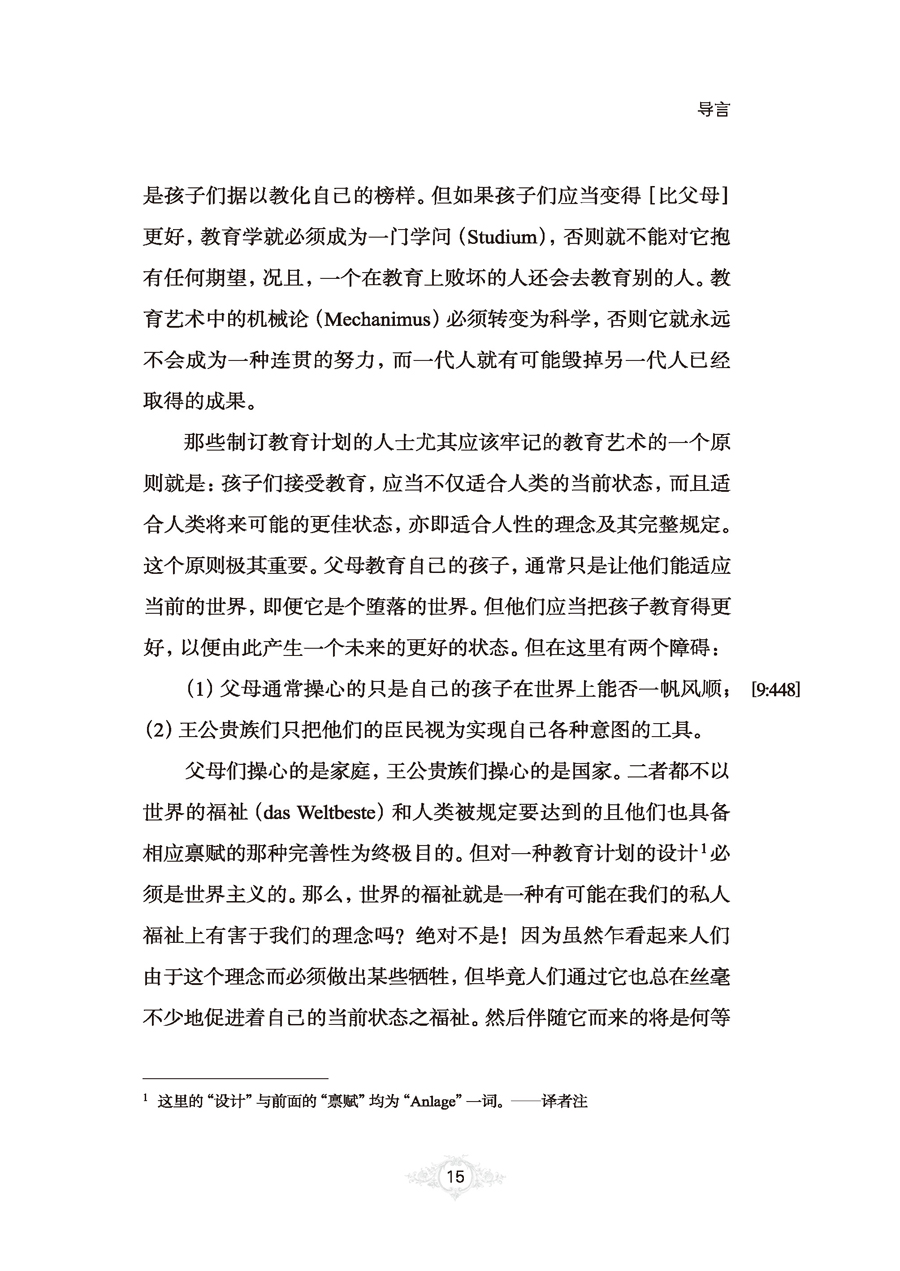教育名著
教育名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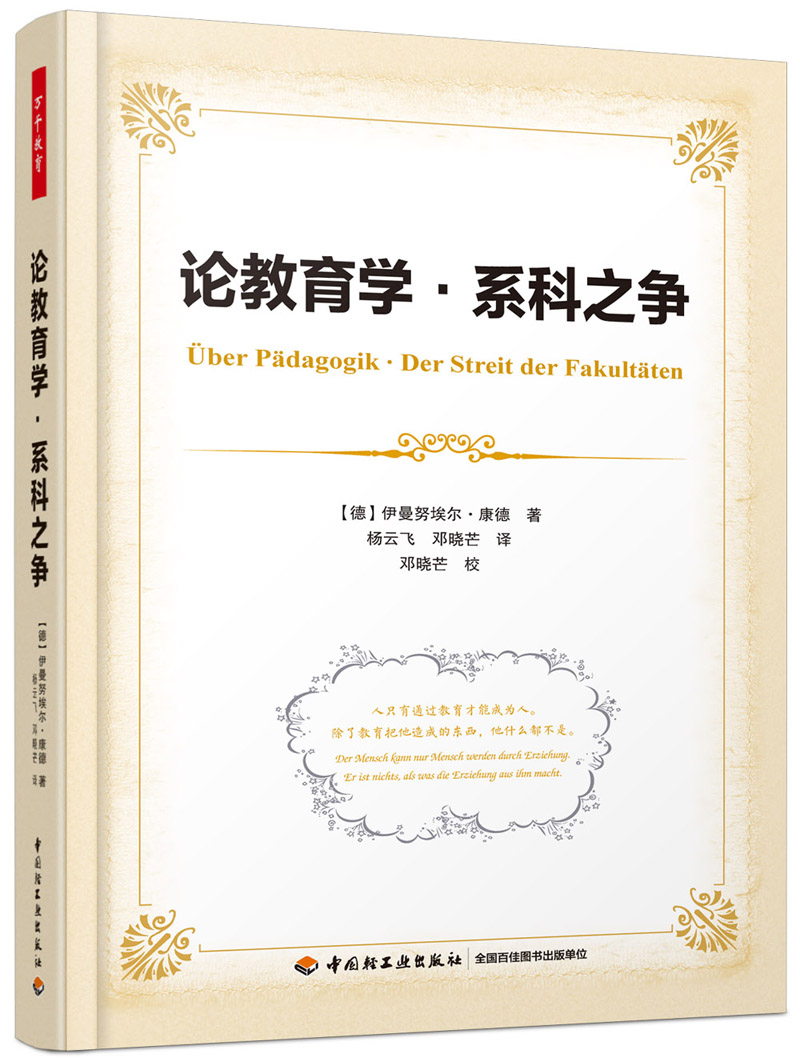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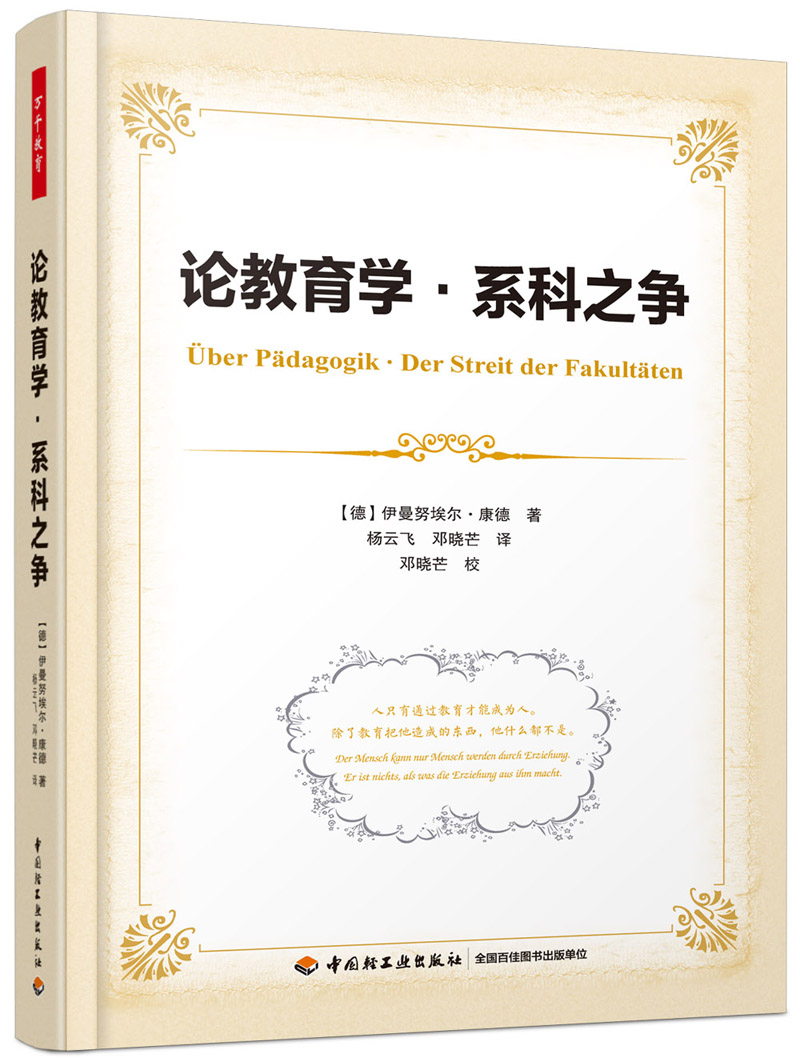

《论教育学·系科之争》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教育学代表作。它由《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两部作品组成。前者集中讨论的是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二者结合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康德的教育思想。
康德把儿童教育分为“自然的教育”和“实践的教育”,主张“从儿童到青年,一切都要向着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努力”,深刻反映了其建立于实践理性之上的道德哲学。就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来说,康德着重探讨了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与哲学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才是统揽一切的学科,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而教育的根本就是哲学教育。
本书由我国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教授和其弟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博士历时一年多精心翻译。邓晓芒教授撰写的精彩的“译者导读”,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略康德的教育思想精髓。该书适合高等院校教育学和哲学专业师生、中小学教师和相关研究者阅读。
康德是伟大哲学家中的教育家,也是伟大教育家中的哲学家。在康德的眼里,教育的根本是哲学教育,教育问题说到底是哲学问题。《论教育学•系科之争》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层面展示了康德教育学思想的全貌,有助于我们对康德基于实践理性的教育哲学做出贯通的考察。
哲学大家的著作,由哲学大家来翻译和解读才给力。因此,万千教育约请国内权威的康德研究专家、我国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教授领衔根据德文版翻译康德的这部教育学巨著。译者在书中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邓晓芒教授还倾情撰写了“译者导读”。此译本既保留了康德的语言风格和文本的学术研究价值,又尽量做到了使读者易于理解。
本书系万千教育策划的“世界教育经典名著丛书”之一,适合对康德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译者导读
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其实按照他的观点,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 康德在1793年致卡·弗·司徒林的信中说:“在纯粹哲学的领域中,我对自己提出的长期工作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②我应做什么?(道德学)③我该希望什么?(宗教学)接着是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而在《逻辑学讲义》(1800)中他明确提出,所有前三个问题都与人类学有关。 而按照当时盛行的看法,人是教育的产物,且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经验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在这方面,康德受卢梭的影响极深,据说他唯一一次打破平生机械遵守的作息习惯,没有在下午准时出门散步,就是因为通宵看卢梭的教育学代表作《爱弥儿》忘了时间。康德生活的18世纪被称为德国历史上的“教育学的时代”2 参看: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429.,普鲁士当局在世界上首次颁布了强迫义务教育的法令,巴泽道在德绍创办的博爱学校以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孩子,在整个欧洲都影响巨大,并得到康德的极力推崇。康德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当过9年的家庭教师,先后在三个家庭教12岁以下的男孩,有丰富的幼儿教育经验;后来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教师,从讲师做到正教授,有四十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这些都使他具备充分的资格来谈论教育问题。他一度还当过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对当时德国教育的现状和弊病了如指掌,并积极思考改进之道。本书将康德的《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集结起来编为一册,前者集中讨论的是儿童教育的问题,后者则主要涉及大学教育和社会大众教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康德的教育思想。
康德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建立于实践理性之上的道德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要用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他的教育观,那就是从儿童到青年,一切都要向着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努力。就儿童教育来说,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的教育”和“实践的教育”。所谓自然的教育,就是一方面对儿童进行初步的纪律规范,不能纵容和放任自流(消极方面);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去尝试、摸索和发展自己的自然能力,不能人为束缚或越俎代庖(积极方面)。所谓实践的教育,就是除了学习生活的技能和与人打交道的处世方法外,还必须教给孩子运用自己所培养起来的自然能力,特别是按照准则行动的能力,去建立起善恶和义务的观念,以便经过道德教育而通往宗教,真正的宗教教育是属于道德性的。可见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他主要是吸收了卢梭的自然主义的教育观,但同时也融入了理性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规训观念,并且从当时的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和巴泽道那里接受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具体的教育细节上,他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例子,说明在孩子哭闹时应该怎么办,在他们说谎时应该怎么办,在孩子欺负别人、歧视佣人时如何对待,如何培养他们勇敢坚毅的性格,等等,这些贯穿着启蒙理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的教育观,对于今天的家长和教师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但也有由于他的新教虔敬主义背景而带来的过于严峻的偏向,例如他反对“寓教于乐”的游戏式教学,甚至反对孩子看小说。在青春期的性教育上,他主张通过严肃坦率的交谈而在适当的时候让青少年获得性知识,同时又让他们意识到过早关注这方面不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主张通过积极的工作和学习来转移注意力,为将来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做好准备。奇怪的是,他认为青少年手淫要比发生性关系更糟糕,因为后者是自然的,前者则是不自然的。但他主张真正健康的性关系应该建立在对异性的敬重之上。他看重的是青年应该形成独立自尊的人格,不要按照别人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己,而要初步树立自己的法权原则,即权利意识和公平意识。
就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来说,康德着重探讨的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与哲学系之间的关系。他把各个系科分为由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组成的“上层系科”,以及哲学系这种“下层系科”。所谓“上层(obere)”和“下层(untere)”,是按照官办大学的意识形态管控来分类的,上层就是和官方较近、能直接执行官方意志的系科,而下层则是比较民间的、由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凭借理性和法则建立的系科,所以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人将之译作“高等学科”和“低等学科”,其实康德并不认为哲学是低等学科,相反,他认为哲学才是最高等的,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但在当时的普鲁士教育体制下,哲学系是最受压制的,被视为一切动乱之源。康德在承认国家对大学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权限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巧妙地与现行制度周旋,尽一切可能扩展哲学系的权限和自由思想的空间。他主张,尽管在维护政府的绝对权威以保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和身体健康方面,起动摇和破坏作用的一切争执都是“非法的”;但在学术问题上,仍然可以由专家学者在系科间进行“合法的”争执,政府不得干预,否则是有失政府尊严的。康德认为哲学层面上的学术争论并不会引发民众的思想混乱,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关心这些抽象理论;但同时,这种争论对于厘清其他各系科的原理,尤其是揭示出这些原理底下的道德本质,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从长远来看,这种争执甚至对政府本身的长治久安也是有实际好处的。
首先,宗教教育真正说来应该是道德教育,其他那些外在的形式和崇拜仪式都是第二位的,只有引进门的作用,而绝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引发无止境的教派斗争。只有作为道德教育的宗教才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且是基督教在历史上多次由于内部分裂和信仰滑坡而走向消沉时能够重新崛起的主要依据。康德在神学系和哲学系之争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和分析占了整个《系科之争》一半的篇幅,他努力要证明的是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所阐明的原理,即只有“道德的宗教”,而没有什么“宗教的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以道德为基础才是真正的宗教,因此宗教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所批示的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沃尔纳对康德的申斥使他耿耿于怀,他将这一批示及他自己的答辩原文在前言中公之于众。可以看出,他的答辩辞虽然在最后服软,保证“作为国王陛下您最忠实的臣民”不再谈论宗教问题,但在原则问题上依然态度强硬,丝毫没有让步。他申辩说,自己作为青年导师是合格的,而作为“民众导师”也是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于国家宗教的。而其中的一个注释则更是以调侃的口气表示,他当年的这一保证在国王逝世之后的今天已经失效了,因为他已经是新国王的臣民了。
其次,法学教育作为使人类在历史中日益趋向改善和进步而设计出来的公民宪政教育,本身的理论也是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只有以道德哲学的眼光,我们才能看出人类历史中的确有一种在道德上不断改善进步的倾向,也才能在这一预设和希望的理念之下确定我们应该遵守的公民社会法则。虽然在人类的经验中这一前景似乎只能诉之于神秘主义的预测或预卜,但凭借实践理性的哲学眼光,我们能够对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类历史事件的经验洞若观火,看出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天意”,也就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法学系绝不只是学习一些法律条文,也不只是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案例,而是必须通过对民众的启蒙而在其头脑中建立某种合乎道德法则的社会理想,哪怕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却可以用作标准来批判现存社会的缺陷并谋求改进之道,即通过不断增加的“合法性”而日益逼近理想中的“道德性”。因此“预卜的人类历史”并不只是巫师和先知的特权,也是哲学家的使命。康德在这里已经预先提出了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待乌托邦理想的原则。
最后,医学系研究的是有关人的身体健康的学问,即养生学和治疗学,由于其本身属于自然科学,所以政府部门的职责只在于监管,而不能干预其自然研究。但康德仍然竭力想要在其中找出人类心灵的哲学原理来为人类祛病养生提供根据。他以自己如何通过对意念的控制来克服失眠、消除病状的个人经验试图证明,一个内心健康的人也能够做到身体上保持健康。当然他这方面的论证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对这一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似乎也没有充分的自信,但至少展示了一位哲人是如何做到身心的最佳统一的。
总之,在康德眼里,所谓教育的根本就是哲学教育,哲学系是一所大学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系科,因为它所从事的是理性的事业,也是自由的事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有道德的人格。这让我想起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我国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院士的名言:“一流的工科必须有一流的理科,一流的理科必须有一流的文科,一流的文科必须有一流的哲学。” 这是校内流传的原始版本,是1996年杨叔子任校长期间创办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时说的,与目前公开出版和网上流传的说法有点出入。 然而,这些年来,素质教育在中国已经变质了,一讲素质教育,人们想到的就只是一些类似于“课外活动”的东西,如琴棋书画、古典戏曲、服饰审美、诵经演礼,再学点希腊文、拉丁文,无须精通,只要能显摆一下,就号称“博雅教育”。至于哲学,学生们则一直都避之唯恐不及。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像样的哲学思想,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只能被禁锢于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培养不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们培养的学生大多要么是头脑狭隘的工具,要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这就不难理解,在我们这里哲学系成了如同康德时代的神学系那样的“上层系科”,即自上而下地论证和灌输某些既定教条的机构,却缺乏诉诸人的健全理性并能够与上层系科进行“合法争执”的、作为“下层系科”的哲学系科。所以读康德的教育哲学,我们会有很强烈的现实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反思。
导言
人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被造物。我们所理解的教育(Erziehung),是指照管(抚养、供养)、规训(训诫)和连同教化一起的教导(Unterweisung)。据此,人依次是婴儿、子弟和学徒。
动物只要拥有某种力量,就会合乎规则地,也就是说,以不会损害自身的方式使用其力量。这的确值得惊叹,例如,人们发现,刚刚破壳而出、眼睛尚未睁开的雏燕,就丝毫不差地知道要让自己的粪便落到鸟巢之外。因此,动物不需要照管,至多需要食物、温暖和引导,或者一定的保护。大多数动物的确需要喂养,但不需要照管。人们把照管理解为父母的保护措施,即不让孩子有害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例如,如果动物也像人类婴孩所做的那样,一来到世上就啼哭,就必定会成为被它的哭声引来的狼或别的野兽的猎物。
规训或者训诫(Disziplin oder Zucht)把动物性转化成人性。一个动物通过它的本能就已然是其全部;一个外在的理性【应指造物主。——译者注】已经为它安排好了一切。人则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他没有本能,而必须自己给自己制订其行为的计划。但是,由于他并非生来就能这样做,而是赤条条地(roh)降生于世,所以必须由其他人来为他做这件事。
人类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人性的全部自然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地从自身发展出来。一个世代教育下一个世代。然而,人们既可以在一个赤条条的状态中,也可以在一个完善的、被培养成的状态中寻求最初的开端。如果后一种状态被假定为在先的和一开始就存在的,那么人必定是后来重新变得野蛮并堕落到粗痞的。
规训防止人由于动物性的驱动而偏离其使命,即人性。例如,规训必须限制人,使其不至于毫无顾忌地、轻率地去冒险。因此,训诫是纯然否定性的,也就是说,是从人身上消除野性的行动;与此相对,教导则是教育的肯定性部分。
野性就是不受法则影响。规训将人置于人性的法则之下,并由此开始让他感受到法则的强制。但这必须及早进行。因此,人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这种意图,即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某件事,而是让他们能够习惯于安静地坐着,严格遵守事先给他们规定好的东西,以使他们不会在将来一有某个想法,就真的并且眨眼间付诸行动。
但是,人对自由天生就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倾向,以至于他只要有一段时间习惯于自由,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也必须像前面说的那样及早施行,因为一旦没有这样做,到后来就很难改变人了。他就会随性而为。人们在各野蛮民族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他们长时间地服务于欧洲人,却从来不适应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但在他们那里,这却并不像卢梭和其他人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对自由的高贵的趋向,而是由于动物尚未在某种程度上在自身中发展出人性来的某种粗痞性(Rohigkeit)。因此,人必须尽早使自己习惯于服从理性的规范。如果人们使某个人在幼年时放任其意志,对其不加任何遏制,则他就会终其一生保有某种野性。而那些在幼年时受到母亲过分溺爱娇惯的人,也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一旦让他们进入世事纷扰之中,他们从此就只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抵制,并到处受挫。
这是一种在上流人物的教育中常犯的错误:因为他们注定要做统治者,所以在其年幼时,人们也就从未真正地阻止过他们。由于人具有对自由的倾向,打磨掉其粗痞性是必要的;相反,动物由于其本能,就不需要这种打磨。
人需要照管和教化。教化本身包含着规训和教导。据我们所知,动物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除了鸟类学习歌唱之外,没有哪种动物从年老者那里学到什么东西。鸟类的歌唱是由年老者教会的,如同在学校里一样,年老者倾其全力为幼鸟示范,而幼鸟则努力从其稚嫩的喉咙中发出同样的音调,这看起来颇为感人。为了证明鸟类不是出自本能而歌唱,它们确实是学来的,值得花功夫去做一个实验:把金丝雀巢里的卵取走一半,然后把麻雀的卵放进去,或者也可以直接把麻雀与金丝雀的雏鸟调换。如果人们把这些麻雀的雏鸟放到一个房间里,使它们听不到外面麻雀的叫声,它们就会学习金丝雀的歌唱,人们就得到会[像金丝雀一样]歌唱的麻雀了。事实上这也是很值得惊奇和赞叹的,即每一种鸟都世世代代保持某种主要的歌声,而这种歌唱的传统大概是世界上最忠实的传统了。【康德在这里针对麻雀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动物身上。于是我们会注意到,例如,从小就被捕捉来的狮子永远不能够完全像成年狮子和后来才被剥夺自由的狮子那样咆哮。但在这个例子中还必须查明的是,这里面有多少应该算到改变了的生活方式的账上,这种生活方式不能不对一个还未长成的机体、对一个尚未完成教养的动物造成影响。在此针对麻雀所说的也只是有限度地有效。我们从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把麻雀的歌唱听成一只真正的金丝雀的歌唱。Naturam furca expellas, et tamen usque recurrit. [译者按:此处为拉丁文,可译为:“你用棍子驱逐自然,但它还会回来。”语出贺拉斯《书简》1, 10, 24.]甚至在鸟类的变种那里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参看:吉尔坦纳(Girtanner),《论康德的自然历史原则》,哥廷根,1796年,第341页。——林克注】
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把他塑造成的东西,他什么都不是。需要注意的是,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因此,某些人身上规训和教导的欠缺,又使得他们成为其学生的糟糕的教育者。而一旦有一个更高类型的存在者【Ein Wesen hherer Art,指神圣的存在者。——译者注】来操心我们的教育,人们就终究会看到,人能够成为什么。但既然教育一方面是教给人某些东西,另一方面只是在他身上发展出某些东西,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在他身上自然禀赋能够达到什么地步。假如在这里至少通过上流人物的支持,通过众人的合力做一项实验,那么这个实验也就已经能告诉我们,人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对于思辨的头脑来说一个同样重要、就像对于博爱主义者来说同等悲哀的一个发现,就是看到上流人物通常总是只关心自己,而不是以能使自然更进一步接近完善的方式,参与到教育的这项重要的实验中去。
没有哪个在幼年时缺乏管教的人,在长大后不会自己觉悟到,他在规训或在教养【原文为Kultur,主要指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译者注】(人们可以这样来称呼“教导”)方面曾被疏忽过。未受教养的人是赤条条的,未受规训的人是野蛮的。耽误规训是一种比耽误教养更大的弊端,因为教养还可在以后再弥补,但野性却无法去除,规训的疏忽是永远无法补救的。也许,教育会逐渐改善,每一代后人都将向着人性的完善更趋近一步;因为在教育(Edukation)背后,隐藏着人类本性的完善性的伟大秘密。从现在起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了。因为人们现在才开始正确地判断和清楚地看出,真正说来什么属于好的教育。设想人的本性将通过教育而发展得越来越好,而且人们能够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这是令人陶醉的。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来更加幸福的人类的前景。
对一种教育理论的筹划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即便我们无法马上实现它,也无损于其崇高。哪怕在实现它时出现重重困难,人们也绝不能马上把这一理念看作幻想,并给它一个美梦的坏名声。
一个理念不是别的,无非是关于—种在经验中尚不存在的完善性的概念。例如,一个完善的、按照正义的规则来管理的共和国的理念!它因此就是不可能的吗?我们的理念首先必须是正确的,然后它才绝非不可能的,无论在其执行过程中会有多少障碍挡道。例如,假如每个人都说谎,说真话就因此而成了一种纯然的怪念头吗?那种要把人身上所有自然禀赋都发展出来的教育理念,当然是真实的。
就当前的教育来说,人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存在的目的。毕竟人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啊!只有当他们按照同样的原理行动,并且这些原理必须成为他们的另一种本性时,他们之间才能步调一致。我们可以制订一种更合乎目的的教育计划,并把对这种教育的指示传给能够逐步地实现它的后代。以报春花为例,我们看到,如果人们从根部移栽它们,所得到的所有的花都只有同一种颜色;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播种它们的种子,所得到的花就具有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颜色。因此,自然已经把胚芽置于它们里面,而要使这些胚芽从中发展出来,则仅仅取决于恰当的播种和移植。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