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评推荐
书评推荐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其实按照他的观点,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在1793年致卡·弗·司徒林的信中说:“在纯粹哲学的领域中,我对自己提出的长期工作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②我应做什么?(道德学)③我该希望什么?(宗教学)接着是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二十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而在《逻辑学讲义》(1800)中他明确提出,所有前三个问题都与人类学有关。 而按照当时盛行的看法,人是教育的产物,且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经验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在这方面,康德受卢梭的影响极深,据说他唯一一次打破平生机械遵守的作息习惯,没有在下午准时出门散步,就是因为通宵看卢梭的教育学代表作《爱弥儿》忘了时间。康德生活的18世纪被称为德国历史上的“教育学的时代”,普鲁士当局在世界上首次颁布了强迫义务教育的法令,巴泽道在德绍创办的博爱学校以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孩子,在整个欧洲都影响巨大,并得到康德的极力推崇。康德出身贫寒,大学毕业后当过9年的家庭教师,先后在三个家庭教12岁以下的男孩,有丰富的幼儿教育经验;后来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教师,从讲师做到正教授,有四十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这些都使他具备充分的资格来谈论教育问题。他一度还当过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对当时德国教育的现状和弊病了如指掌,并积极思考改进之道。本书将康德的《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集结起来编为一册,前者集中讨论的是儿童教育的问题,后者则主要涉及大学教育和社会大众教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康德的教育思想。
康德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建立于实践理性之上的道德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要用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他的教育观,那就是从儿童到青年,一切都要向着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努力。就儿童教育来说,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的教育”和“实践的教育”。所谓自然的教育,就是一方面对儿童进行初步的纪律规范,不能纵容和放任自流(消极方面);另一方面要让他们去尝试、摸索和发展自己的自然能力,不能人为束缚或越俎代庖(积极方面)。所谓实践的教育,就是除了学习生活的技能和与人打交道的处世方法外,还必须教给孩子运用自己所培养起来的自然能力,特别是按照准则行动的能力,去建立起善恶和义务的观念,以便经过道德教育而通往宗教,真正的宗教教育是属于道德性的。可见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他主要是吸收了卢梭的自然主义的教育观,但同时也融入了理性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的规训观念,并且从当时的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和巴泽道那里接受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具体的教育细节上,他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例子,说明在孩子哭闹时应该怎么办,在他们说谎时应该怎么办,在孩子欺负别人、歧视佣人时如何对待,如何培养他们勇敢坚毅的性格,等等,这些贯穿着启蒙理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的教育观,对于今天的家长和教师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但也有由于他的新教虔敬主义背景而带来的过于严峻的偏向,例如他反对“寓教于乐”的游戏式教学,甚至反对孩子看小说。在青春期的性教育上,他主张通过严肃坦率的交谈而在适当的时候让青少年获得性知识,同时又让他们意识到过早关注这方面不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主张通过积极的工作和学习来转移注意力,为将来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做好准备。奇怪的是,他认为青少年手淫要比发生性关系更糟糕,因为后者是自然的,前者则是不自然的。但他主张真正健康的性关系应该建立在对异性的敬重之上。他看重的是青年应该形成独立自尊的人格,不要按照别人的价值标准来评价自己,而要初步树立自己的法权原则,即权利意识和公平意识。
就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来说,康德着重探讨的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与哲学系之间的关系。他把各个系科分为由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组成的“上层系科”,以及哲学系这种“下层系科”。所谓“上层(obere)”和“下层(untere)”,是按照官办大学的意识形态管控来分类的,上层就是和官方较近、能直接执行官方意志的系科,而下层则是比较民间的、由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凭借理性和法则建立的系科,所以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人将之译作“高等学科”和“低等学科”,其实康德并不认为哲学是低等学科,相反,他认为哲学才是最高等的,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但在当时的普鲁士教育体制下,哲学系是最受压制的,被视为一切动乱之源。康德在承认国家对大学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权限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巧妙地与现行制度周旋,尽一切可能扩展哲学系的权限和自由思想的空间。他主张,尽管在维护政府的绝对权威以保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和身体健康方面,起动摇和破坏作用的一切争执都是“非法的”;但在学术问题上,仍然可以由专家学者在系科间进行“合法的”争执,政府不得干预,否则是有失政府尊严的。康德认为哲学层面上的学术争论并不会引发民众的思想混乱,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关心这些抽象理论;但同时,这种争论对于厘清其他各系科的原理,尤其是揭示出这些原理底下的道德本质,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从长远来看,这种争执甚至对政府本身的长治久安也是有实际好处的。
首先,宗教教育真正说来应该是道德教育,其他那些外在的形式和崇拜仪式都是第二位的,只有引进门的作用,而绝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引发无止境的教派斗争。只有作为道德教育的宗教才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且是基督教在历史上多次由于内部分裂和信仰滑坡而走向消沉时能够重新崛起的主要依据。康德在神学系和哲学系之争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和分析占了整个《系科之争》一半的篇幅,他努力要证明的是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所阐明的原理,即只有“道德的宗教”,而没有什么“宗教的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以道德为基础才是真正的宗教,因此宗教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所批示的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沃尔纳对康德的申斥使他耿耿于怀,他将这一批示及他自己的答辩原文在前言中公之于众。可以看出,他的答辩辞虽然在最后服软,保证“作为国王陛下您最忠实的臣民”不再谈论宗教问题,但在原则问题上依然态度强硬,丝毫没有让步。他申辩说,自己作为青年导师是合格的,而作为“民众导师”也是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于国家宗教的。而其中的一个注释则更是以调侃的口气表示,他当年的这一保证在国王逝世之后的今天已经失效了,因为他已经是新国王的臣民了。
其次,法学教育作为使人类在历史中日益趋向改善和进步而设计出来的公民宪政教育,本身的理论也是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只有以道德哲学的眼光,我们才能看出人类历史中的确有一种在道德上不断改善进步的倾向,也才能在这一预设和希望的理念之下确定我们应该遵守的公民社会法则。虽然在人类的经验中这一前景似乎只能诉之于神秘主义的预测或预卜,但凭借实践理性的哲学眼光,我们能够对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类历史事件的经验洞若观火,看出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天意”,也就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法学系绝不只是学习一些法律条文,也不只是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案例,而是必须通过对民众的启蒙而在其头脑中建立某种合乎道德法则的社会理想,哪怕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却可以用作标准来批判现存社会的缺陷并谋求改进之道,即通过不断增加的“合法性”而日益逼近理想中的“道德性”。因此“预卜的人类历史”并不只是巫师和先知的特权,也是哲学家的使命。康德在这里已经预先提出了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待乌托邦理想的原则。
最后,医学系研究的是有关人的身体健康的学问,即养生学和治疗学,由于其本身属于自然科学,所以政府部门的职责只在于监管,而不能干预其自然研究。但康德仍然竭力想要在其中找出人类心灵的哲学原理来为人类祛病养生提供根据。他以自己如何通过对意念的控制来克服失眠、消除病状的个人经验试图证明,一个内心健康的人也能够做到身体上保持健康。当然他这方面的论证并没有多少说服力,他对这一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似乎也没有充分的自信,但至少展示了一位哲人是如何做到身心的最佳统一的。
总之,在康德眼里,所谓教育的根本就是哲学教育,哲学系是一所大学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系科,因为它所从事的是理性的事业,也是自由的事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有道德的人格。这让我想起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我国素质教育的倡导者杨叔子院士的名言:“一流的工科必须有一流的理科,一流的理科必须有一流的文科,一流的文科必须有一流的哲学。” 这是校内流传的原始版本,是1996年杨叔子任校长期间创办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时说的,与目前公开出版和网上流传的说法有点出入。 然而,这些年来,素质教育在中国已经变质了,一讲素质教育,人们想到的就只是一些类似于“课外活动”的东西,如琴棋书画、古典戏曲、服饰审美、诵经演礼,再学点希腊文、拉丁文,无须精通,只要能显摆一下,就号称“博雅教育”。至于哲学,学生们则一直都避之唯恐不及。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像样的哲学思想,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只能被禁锢于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培养不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们培养的学生大多要么是头脑狭隘的工具,要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这就不难理解,在我们这里哲学系成了如同康德时代的神学系那样的“上层系科”,即自上而下地论证和灌输某些既定教条的机构,却缺乏诉诸人的健全理性并能够与上层系科进行“合法争执”的、作为“下层系科”的哲学系科。所以读康德的教育哲学,我们会有很强烈的现实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反思。
本书中的《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已有李秋零的中译本,分别载于所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和第7卷。《系科之争》的第二篇“哲学系与法学系的争执”也已有何兆武先生和李明辉先生的译文(前者载于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后者载于李明辉译《康德历史哲学文集》)。我们之所以要将这两部分合起来再出一个关于教育学的译本,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两部分分散在两个不同的集子中,体现不出康德教育学思想的全貌(即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利于对康德的教育哲学做贯通的考察。而这次翻译,我们依据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和第9卷,对照其他几个德文版和英文版,对已有的中译本进行了全面的再推敲。我们发现,康德的这两个文本篇幅不大,但翻译的难度却相当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康德的“三大批判”还难译。因为它们不但保持着“三大批判”中那种冗长烦琐的文风,而且有在谈论经验事物时的那种机智和风趣,再加上当时深厚的人文背景和康德渊博的知识面,这就使我们在翻译一些句子时颇费思量,很多意思要凭体会和猜测,也增加了不少考证和查找的工夫。而康德在本书中表达整体思想时也不像他的正式体系那样直截了当,更多的是转弯抹角、含沙射影,这也增加了我们理解的难度。再加上与已有中译本进行反复对照,翻译这本不到13万字的小册子耗费了我们不少的时日,所花时间比我们翻译康德的其他主题较为单纯的著作至少要多两倍。本书由杨云飞副教授译出初稿(因杨老师后期患重感冒,其中《系科之争》的第一篇最后部分从“系科之争的和平协定和调解”起的1万字以及第三篇“哲学系与医学系的争执”的1.4万字由我翻译补上),由我全面校对,最后再由我统稿,并为两个文本分别做了德汉词汇索引和汉德词汇对照表。由于最后统稿工作由我完成,因此译文中凡有不当之处均由我负责,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邓晓芒
2018年1月20日于喻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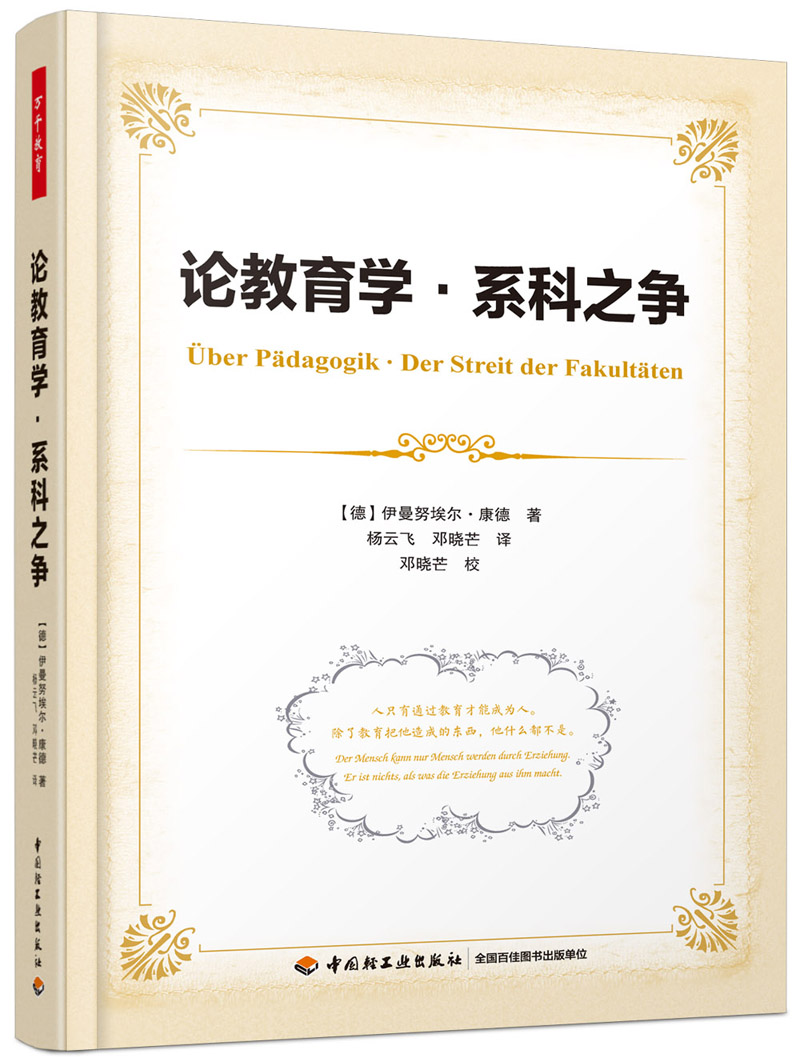
《论教育学·系科之争》
(德)伊曼努埃尔·康德 著
杨云飞,邓晓芒 译
邓晓芒 校
万千教育出品图书在各大网店均有售
(当当、亚马逊、京东、天猫……)
【个人购书】请移步各大网店自主购买
【团购图书】请拨打以下电话联系购买
手机号(同微信号):18610088465 / 座机:010-65181109
团购图书有优惠,团购图书有优惠,团购图书有优惠。